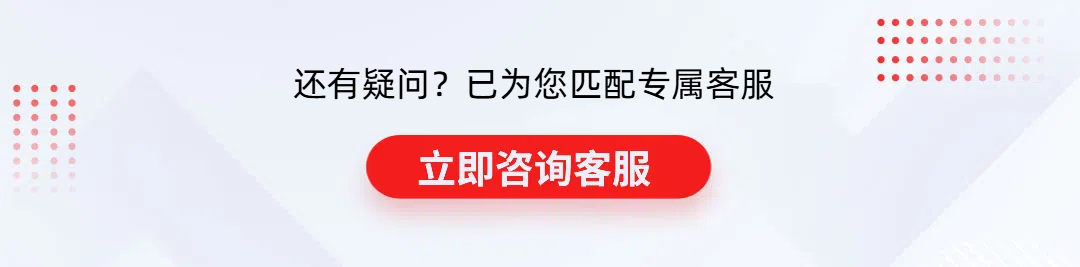“季诺维也夫信”事件,《每日邮报》和《泰晤士报》的协同作战可以说是英国政府争取国际新闻话语权的典范。
非主流媒体引发民间舆论场,构造统一的国内舆论环境;主流媒体再次验证非主流媒体的观点,遥相呼应,形成统一口径对外报道,以“受害者”的姿态博取国际同情,构造与国内相统一的国际舆论环境,将单一官方渠道发布消息的苏联击溃于无形。
这给当下我国争夺国际新闻话语权带来启示。
所谓话语权包括话语实力和话语权力。
前者是指具有足够的信息资源、传播途径进行国际政治新闻报道,后者是指传播作用力、传播效果。
我国的主流媒体在这两方面的优势可见一斑,但是在非主流媒体方面的建构也存在着和苏联一样的问题,这也是我国媒体为西方国家所诟病的地方。
对比苏联,我国对非主流媒体的重要性尚不够重视,在国际话语权的争夺上主要依靠主流媒体发声,与西方国家的统一战线相比,明显逊色很多。
结合“季诺维也夫信”事件和中国实际,笔者认为我国目前在国际新闻话语权的争夺上主要存在以下缺陷。
第一,单一的媒介文化建构模式,信源单一,发声渠道单一,浓烈的官方色彩,难以获得国际社会的认可。
第二,对于西方媒体的“对抗式”解读,没有形成自己的国际新闻话语体系与之进行对抗,容易陷入西方价值观体系。
第三,对外传播过于倾向于正面宣传,一个没有负面报道的国家自然是难以令人信服的。
第四,传播方式和技巧不能因时因地制宜,不能实现“国内故事,国际表达”。
第五,主流媒体与非主流媒体资源分配严重不均,呈断裂式发展,在形成国内统一对外口径方面明显不足。
第六,政党报刊体制色彩过于浓厚,缺乏市场竞争的压力,新闻内容过于模式化。
第七,新闻自由与言论自由受到的限制过大,不利于多元观点的形成。
针对我国国际新闻话语权存在的问题,以及非主流媒体对构建国际话语权的重要性,笔者提出以下建议:
其一,充分发挥主流媒体与非主流媒体的联动优势,一致对外,增加“国际新闻发声量”;其二,国际新闻报道要“国内故事、国际表达”,采取跨文化传播方式;其三,主流媒体要强化“文化符号”,弱化“政治”,而非主流媒体则相反,加强二者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共识;其四,构建扎根于民族文化的国际话语体系,有纲有则方能临危不乱;其五,在现如今新媒体技术等发展的情况下,要充分发挥好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的优势,使二者都能成为国际新闻话语权的主力军。
 公司注册
公司注册 
 银行开户
银行开户  记账报税
记账报税  年检审计
年检审计  VAT注册
VAT注册  商标注册
商标注册  专利申请
专利申请  著作权登记
著作权登记  电商入驻
电商入驻  网站建设
网站建设  公证认证
公证认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