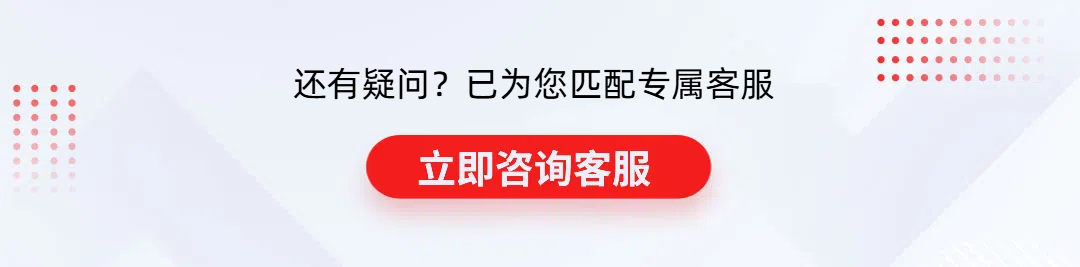科技全球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迅速推进,使得生态问题广泛蔓延,并超越国界成为世界各国共同面对的难题,因此,历史呼唤新的文明时代的到来。
当全球性的生态灾害日益威胁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时,认真审视全球性的生态难题及其后果,深入剖析全球化进程中生态文明发展的规律,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积极探讨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现实路径,正确看待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世界性与民族性的关系,就成为我们亟待解决的时代课题。
“五位一体”的生态文明建设总体战略布局的提出对积极推进当前生态文明建设、国家“十二五”环保规划的落实以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实现,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全球性生态危害及其原因
一部人类文明史,就是一部人类与自然相抗争的历史。
如果说,原始文明时期生产力发展的局限使人类只能消极地“顺应”、“敬畏”自然,并对自然顶礼膜拜,农业文明时期神意的授权使人类成为自然的“主人”,能够主动地认识并改造自然,那么,到了工业文明时期,特别是经济全球化的到来,人类似乎成为自然的“征服者”,高举现代科技的利器开始贪婪地攫取自然、役使自然,最终导致全球性的生态环境的急剧恶化:
人口危机、环境危机、粮食危机、能源危机、原料危机等,它超越了阶级、种族、民族和地域的限制,成为蔓延世界的生态难题。伴随着人类历史步入新世纪,这些原本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引起广泛关注的全球性生态难题不仅没有得到有效遏制,反而愈演愈烈。
从哲学的视角进行省思,其原因大致有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传统西方哲学“主客二分”的机械论思维模式成为主导。
西方哲学遵循经验与归纳的逻辑,使主体与客体、思维与存在、人与自然二分对立,主体被认为是脱离自然客体和社会存在的单子,客体
被认为是与主体毫无关涉的客观物质载体。
因此,全球性生态问题的呈现,企服快车面,表明科技理性的膨胀催生了人类的主体性效益,在人类利用自然、攫取自然的进程中充分彰显了人类本质力量的强大;
另企服快车面,人类在无度的开发甚至滥用自然资源的过程中制造了“游离”的责任主体,不文明的消耗和贪得无厌、永无止境的需求招致“类本质”的异化,最终引发了人与自然的分离与对抗。
第二,人类“中心”大行其道。
建立在资本基础上的近代人类中心主义无法立足于人类实践和社会生产方式的变迁考察生态难题,不能根本揭示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发展与全球性生态危机的内在关联,因而也便无从厘清当前全球生态治理中权利、责任和义务的关系,无法对全球性生态危机追根溯源。
然而,“对自然和生态平衡的界定明显是一种人类的行为,一种与人的需要、愉悦和愿望相关的人类的界定”①。
但是,这里的人类“中心”,其“对经济的发展,生态学的态度应当是适度,而不是更多。
应该以人为本,尤其是穷人,而不是以生产甚至环境为本,应该强调满足基本需要和长期保障的重要性。
这是我们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更高的不道德进行斗争所要坚持的基本道义”②。
或许,这种长期的集体主义的人类中心主义和“以人为本”的生态理念是应对生态难题的可行思路。
第三,“科学至上”主义引发的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对峙。
“科技至上”导致“GDP”主义盛行和市场逻辑的主导地位,使全球化的运作和永无止境的占有成为必然,这样的经济逻辑忽视了掌握和运用现代科技的人的作用,不了解生态资源的有限性,不能深刻洞察全球化进程中生态系统日益衰退这一社会现实,是典型的“技术乐观主义”。
而“技术悲观主义”则陷入另一个极端,认为科技的发展和经济增长必然以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唯一的出路就是推行“零发展”、“零增长”、“负增长”的经济发展模式,甚至全面否定全球化的进程,否定科技的推进和经济的发展在造成人类与生态环境矛盾的同时也包含着不断化解矛盾,实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可能性。
第四,资本主义制度的矛盾日益显露。
以资本为逻辑的社会经济运行机制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突出特征,“支配着生产和交换的一个一个资本家所能关心的,只是他们的行为的最直接的有益效果……出售时要获得利润,成了唯一动力”③。
无限扩张的经济理性遵循“核算和效率”的运作逻辑,“这样一来,资本主义投资商在投资决策中短期行为的痼疾便成为影响整体环境的致命因素”④。
由此,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是私欲膨胀以及人与人之间利益争夺的根源。
因此,“最根本的是要消除私有财产权力在人与人之间制造出来的竞争和对抗,在此基础上消除不同利益主体在利益上的冲突。
只有如此,人们才能真正从人的‘类存在’的意义上去关注那些属于人类的共同利益,否则,要真正解决生态问题是不可能的”⑤。

 公司注册
公司注册 
 银行开户
银行开户  记账报税
记账报税  年检审计
年检审计  VAT注册
VAT注册  商标注册
商标注册  专利申请
专利申请  著作权登记
著作权登记  电商入驻
电商入驻  网站建设
网站建设  公证认证
公证认证